
在这繁华的都市中,诺基亚的彩铃声伴随着我,仿佛诺基亚也在歌唱,而我身着阿玛尼,满怀欢喜地回到故乡。远离了那些所谓的二奶和小三,我的媳妇从此不再忧伤,因为她知道,我已经找到了属于我的方向。
在那个80后的世界里,我下载了许多彩铃,将它们存入史册。我的人生或许并不精彩,但我要让我的手机充满色彩。我选择了爱娃萧亚轩的《最熟悉的陌生人》作为我的铃声,每次响起,都仿佛是对过去的回忆,是对那一夜情酣畅淋漓的反思——我们爱得如此汹涌,爱得如此深,但梦终究会醒,我们会沉默、会挥手,却再也回不到过去。
我总是在特定的时间,掐准了点,等到萧亚轩唱到“如果当初在交会时能忍住了悸动的灵魂,也许今夜我不会让自己在思念里沉沦”中的“交会”时,才会接电话。然而,有一次,有个女孩给我打了三遍手机,我都没有接,不是我不想接,而是我人机分离,根本听不见。后来,她告诉我,萧亚轩都唱到“心碎离开”了,我却还未接电话,她只能“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……”。
在一个“平林漠漠烟如织”的黄昏,我给一个在光华路汉威大厦上班的“女海归”打手机,那时的手机铃声是一段音乐,彭羚超一流怨妇的歌声飘入耳中——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,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。这缭乱的城市,容不下我的痴,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,这样地放肆?
每临黄昏,我都会给这个日本京都“女海归”打手机,渐渐地,约她出来的目的已变得模糊,我只为听她西门子手机给我录播彭羚的《囚鸟》: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,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,对爱无计可施,这无谓的日子,眼泪是唯一的奢侈。
进入深秋,京都“女海归”的手机铃声又变,变成了王靖雯的《红豆》:有时候,有时候,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。可是我,有时候,宁愿选择撅瓶二锅头。宁可无耻不下流,也许你会陪我,撮顿铁板牛柳。
彩铃真好,对我这个歌词爱好者来说,写随笔时,一旦忘了歌词,就给女孩打手机,她们的手机铃声,仿佛就是一首首流行的歌曲,在我耳畔回荡。我现在想找歌词,根本不用在网上搜,直接给女孩打手机。有一次,我为了印证刘若英《为爱痴狂》的歌词,给一个女孩打了好几遍手机,终于给人家打急了,她拽过电话就问我:你是为我痴狂还是为刘若英痴狂?
这样的生活,虽然简单,但却充满了色彩。每一个铃声,每一个声音,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故事,一个关于我们的故事。
转载请注明来自广州玛斯顿影音有限公司,本文标题:《彩铃儿响来玉鸟儿唱 》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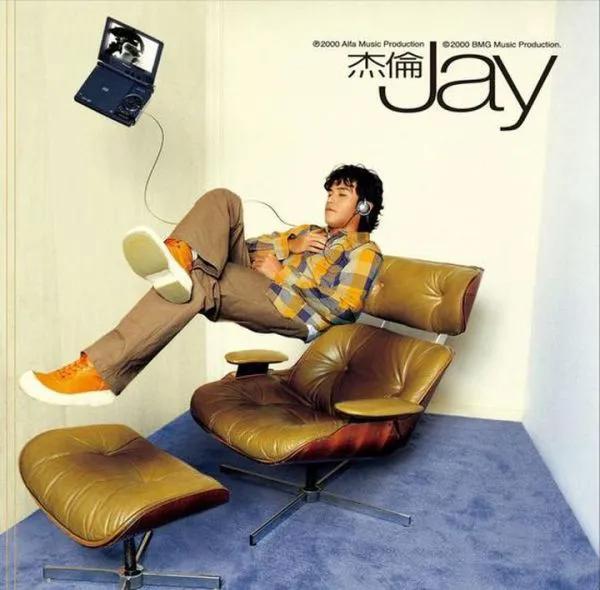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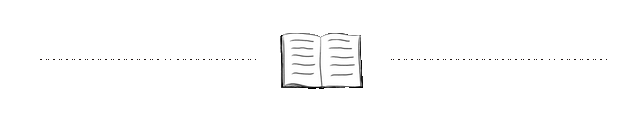





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
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